奉俊昊式类型化叙事中寓言体故事的映射

- 古人在此LV.连长
- 2016/9/13 18:1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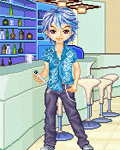
- 憨豆特工
- 2016/9/13 22:41:20
以《怪物》为例论角色映射群体
奉俊昊的第三部长片是《怪物》,上映后一举拿下当年的全国票房冠军,这部以家庭为单位对小女儿展开营救的故事,结构出了一系列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极纯粹的商业类型包装(灾难片)下,饱藏着层层对社会现代文明产物质问。
《怪物》相比于前两部更像是一个被类型化叙事结构包裹严实的寓言故事,层层的比喻、暗喻手法,穿插叠加,最终以“田园式”的伪圆满结局告终,告诉人们“时刻警惕着外来文化的负面侵袭”。
影片开头从怪物的诞生便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主观批判西方外来文化不负责产物的影片。虽然“田园式”的保守结局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偏左观念,但是《怪物》一片,再一次从实践上证明了奉俊昊“偷梁换柱”(价值转换)手法的融会贯通和广泛题材的应用意义。其手法不仅限于悬疑追捕题材,甚至于灾难类型结构中依旧能够游刃有余。
与 2014 年灾难类型片《哥斯拉》①相比,怪物出现后影片的期待值基本都被转移到了主人公和全人类能否继续生存这个问题。《哥斯拉》中,代表人类求生欲望的科学家和人类军事力量在怪物面前虽然是弱小无力的,但其思维本质上一直在积极努力并不断进步,其角色价值始终处在正面。反观奉俊昊的《怪物》,从小女儿丢失之后,社会各界都给予该事件相应的反应,但是所有反应的表现都是愚钝或是荒诞的——小女孩丢失后,医学组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接触过怪物的父亲角色隔离并进行实验,而这个实验的本质目的并不是出于抵抗怪物,而是科学探索、责任医生的对眼形象和荒诞可笑的逻辑思考、负责武装维护人民的军事组织在《怪物》中也始终在做阻力行为(负面价值),其行为上除了隔离人群喷洒消毒剂,就是追捕营救小女孩的一家人。
作为一个在国内学习电影的学生,我最敏感的就是国内电影体质的限制问题,陈凯歌当年的《霸王别姬》辉煌灿烂的背后却掩盖了《蓝风筝》从东京国际电影节拿奖后被禁映的苦苦心酸。文化艺术领域本就该涵盖针对许许多多现实矛盾和文化反思的探究。电影作为一种当下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媒介,本身就该具有发问、探究等职能。国内影片放映体制的限制,从某个角度来讲对于电影艺术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侧面的文化传播限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放映限制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反方面却极大地影响影视创作者成长发展的空间。奉俊昊作为一个韩国电影人,他是优秀且幸运的。
《怪物》也好,《杀人回忆》也罢,乃至《绑架门口狗》和后来的《母亲》,在其作品中出现的任何角色,我们都能够从中发现其出现时所代表的“未解决”观点和经验。
“关于类型生产的价值判断,大概会有如下论述,其一,积极站在电影工业立场上进行讴歌的,因为类型生产模式的建立,几乎是电影工业成熟度的一个标志,它是大片场和明星制所依赖的叙事生产的平台;其二,积极站在电影艺术和文化反思的立场上激烈的抨击类型生产模式,大概指出类型生产的“神话”或者“通话”的实质,强调类型叙事其实根本隔绝了对现实的真正思考,使得电影几乎成为人民的鸦片。但是无论这两个立场你怎么选边站,对于强调“电影”媒介介入社会现实,从而参予社会现实而言,类型生产都是负面意义的。
奉俊昊的电影被笔者关注是因为他的《杀人回忆》。笔者关注这部作品的原因就在于这部当年韩国的票房冠军作品,在一个非常正面意义上让我们可以面对类型叙事资源,让电影可以寻获一种“跨境”制作的可能,就是作者电影和大众文化生产的某种嫁接,虽然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上对于各种观众而言也许依然是各取所需、仁者见仁,但是他毕竟提供了一种沟通讨论的统一平台。《杀人回忆》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部作品使用一个类型叙事的壳(变态杀人狂,譬如《沉默的羔羊》等等)进行了对韩国军政府时期的社会悲剧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在此处,“类型”所具有的消费心理定势的能量释放促使了这种反思直接面对大众,或者说它让严肃的社会议题直接变成建构大众心里的资源,变成一种走出学院或者知识分子圈的可能性,因为所有的观众都要面对“凶手”究竟是谁的迷局。”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