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自己的上帝:哈内克和冰川三部曲

- 慕枫浩LV.连长
- 2016/7/22 16:56:51
文 |柯诺(北京)
编 |央(台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目前一共有7位导演两夺金棕榈:弗朗西斯.科波拉(1974年《窃听大阴谋》、1979年《现代启示录》);今村昌平(1983年《楢山节考》、1997年《鳗鱼》);库斯图里卡(1985年《爸爸去出差》、1995年《地下》);比利.奥古斯特(1988年《征服者佩利》、1992年《善意的背叛》);达内兄弟(1999年《罗塞塔》、2005年《孩子》),以及迈克尔.哈内克(2009年《白丝带》、2012年《爱》)。
在这几位大导演中,哈内克是进入“双金棕榈”俱乐部用时最短(3年两夺),同时也是最“年轻”的导演,倒不是说出生年龄(库斯图里卡、奥古斯特和达内兄弟都比他要小),是进入电影圈的年纪。哈内克在47岁的时候才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这要比很多电影导演晚得多。

- 呵护着你
- 2016/7/22 22:40:24
在戛纳主竞赛的征程上,他也比其他人要来得稳扎稳打,一步一步从《巴黎浮世绘》的最佳编剧,到《钢琴教师》的评委会大奖,到《隐藏摄影机》的最佳导演,再到摘夺两枚金棕榈。哈内克一路追随仰慕戛纳,没有任何一部电影去往冬季的柏林和水城威尼斯,脚下生花,戛纳也回馈了他。 电影之前,哈内克有两个极为重要的艺术生涯:舞台剧和电视电影。
踏进剧场,哈内克得感谢当时的女朋友。哈内克年轻时的女友在德国小镇巴登巴登的剧团里当演员,哈内克给她的表演提了不少建议,女友也认为他对戏剧和表演的理解颇有造诣,在女友的搭桥引荐下,哈内克很快获得剧团团长的青睐并导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舞台剧《整日在林间》,之后陆续排演了很多知名剧作家的剧本,譬如,克莱斯特的《破瓮记》、黑贝尔的《玛丽雅.玛格莲娜》以及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等,其中《阴谋与爱情》这个关于宫廷权力斗争的爱情悲剧,是他自认为最好的一次舞台创作。

- dxdxnhw
- 2016/7/22 20:42:10
当然,也有一些不大成功的作品,对拉比什的滑稽喜剧《三人之中最幸福》的改编最让哈内克受挫,这也让他明白,自己对喜剧的敏锐度和对喜剧手法的转换能力严重不足。喜剧的基本节奏要依托两种语言,一个在对话,另一个则落于肢体动作,哈内克日后的那些电影泛化着现代化的焦虑和困顿,以沉默以对替代大段密集对白,用暴力的施虐,一挥的巴掌对立起喜剧应有的诙谐。哈内克非常了解自己,他明白,适合他的,肯定不是喜剧,更不是悲喜剧,永远也必须是彻头彻尾,一击必杀的冷默悲剧。 70年代,艺术圈认为电视优于剧场。哈内克没有放弃舞台剧,但也将新的目光投向电视荧幕。第一部电视电影《以及其后的... ...》意在向其精神偶像戈达尔致敬,电影以他的语录开场,场景里还故意出现了《男性女性》的海报。另外,从电视电影开始,固定机位的一镜到底,侧面推轨镜头,垂直俯摄等哈内克的标志性运镜清晰可见,这些在《趣味游戏》,《钢琴教师》,《白丝带》中颇为明显的镜头源起于哈内克在电视电影上的不断试炼。

- 真真真
- 2016/7/22 22:49:37
舞台剧和电视电影,这两个时代的历练促使他从第一部电影作品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美学理念,形式风格和一以贯之的叙事特点。今天恰逢迈克尔.哈内克74岁生日,回顾起他最早的三部电影“冰川三部曲”———《第七大陆》、《班尼的录像带》、《机遇编年史的71块碎片》,可以发现,那时在电影界初出茅庐的他,早就有了大师的锋芒。
《第七大陆》:拼写“动词”,解释“毁灭”
在我看来,“冰川三部曲”是哈内克在利用新的实验方法讨论叙事的另一种可能性效益,而第一部《第七大陆》就是他尝试在用“动词”的拼写去解释关于“毁灭”的词义。

- 20077002
- 2016/7/23 0:08:51
“人在摧毁自己之前,先去摧毁这个导致自己毁灭的物质世界”,哈内克依循着这个准则,用近乎一半的电影时长聚焦“乔治”一家三口自杀前反锁屋内,从捣毁物件到毁灭自己的宣泄行为。
哈内克用“断简残篇”的结构来组织“动词”。场景与场景之间用长度不一的黑屏进行区隔、连接,呈现出“碎片化”风格,不仅粘附于时间,还在空间里显现。一系列动作被刻意肢解,被局部于逼仄的画面内,在开篇洗车长镜头过后,就用关闹钟、穿鞋、开门等一个个镜头拼接,在随后的购物、拜访爷爷奶奶等场景里也都采取这样的拍摄方式,意在强调行为的“单调性”和“机械性”,一组组动作特写就像《扒手》里的镜头剪辑方式,宛如布列松现身幕后指导,只是这已然不是在炫耀扒手手指的灵活花招,而是不可捉摸,毫无头绪就迎面袭来的观感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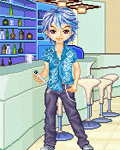
- 憨豆特工
- 2016/7/23 2:17:49
对“动词”的玩法不只有这样。把两种互相矛盾的元素并置在一起是哈内克的一套惯用手法,或可称为“矛盾修辞法”。电影中,把妻子在熟食店买肉的画面和丈夫购买斧头的画面平行剪辑在一起,莫名的冲突性逼出紧张感,再一招刺激视觉疑惑。
剧场年代,哈内克从没搬演过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剧本,在他眼里,剧场演员阻碍了契诃夫的剧本重现,“我觉得我的导演风格似乎不符合那个类型的美学。一开始,我对契诃夫这位剧场之神满怀景仰与钦佩,幻想自己可以导一出与他的天才般配的作品。可是后来,我不知道如何为每个角色找到厉害的演员,组成理想的阵容。正因如此,我们很难看到一出令人信服的契诃夫”。剧场里实现不了,他便在大银幕上践行了契诃夫的创作理念。
契诃夫说过,“如果墙上挂着一把枪,它就一定要打响”。《第七大陆》前半段中,女儿故意装盲,行为被机械拆卸,观看的视野被强行区隔,前期的观感疑惑不过是为达到叙事目的的一套障眼法,是为指向更大幅度的动作施展范围———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暴力和死亡的宣泄!所以,餐桌上的不言不语,妈妈和叔叔的两场意外恸哭也在更强有力的动词描绘中有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

- cassata
- 2016/7/23 7:54:30
“第七大陆”在电影里指向Australia,一个泛指,指向一个中产阶级向往的理想国度,当然也基于现实,1970年到1980年间,的确有一大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移民到澳大利亚。这个理想目标在电影里即便真实也足够虚幻。有这么一个细节,自杀前,女孩随父亲去了废车场,她在那看到了远处海上的轮船,这是喻指着即将驶往理想国度?惊鸿一瞥,我更倾向解读为随之破灭的幻像。
电影里的一家三口,选择自我绑缚,实则被物欲横流的现实紧捆。所以当回过头看他们打破一屋的精致,把一把把钞票冲入马桶,批判对象和表达意图其实已经昭然若揭,说简单粗暴,是的,也真的太直接了。或许表达极端,但也不可否认极端的价值面,它也逼着我们到另一个极端去叩响脑门,从昏迷的物质现实中睁眼,涌出唯物主义者的潮流。

- 分手在1989
- 2016/7/23 6:05:00
主人公班尼(由亚诺.弗里斯奇饰演,在《趣味游戏》里他有着更为惊艳的表演,他饰演的杀人犯傲慢,自大,令人不寒而栗。)是一个对录像充满热情的少年,对暴力文化的热衷让他在一次偶然中用杀猪枪杀死了一个陌生的女孩,令人更为震惊的是,他父母为了保护班尼,秘密处理了尸体,然而,是班尼的一盘录像带曝光了父母的对话,最后三人才绳之以法。
在哈内克的文本里,班尼的暴力倾向和行为的制造机是无处不在的媒体,录影带,电视,杂志皆是班尼这个迷途羔羊的罪魁祸首。班尼在录影带出租店里租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B级恐怖片《毒魔复仇》,在误杀女孩后他看起了迪士尼的唐老鸭漫画,而班尼最爱观赏的录像则是父亲在自家农场里杀猪的影片...对班尼个体的聚焦,这些细节无不阐述着哈内克对媒体的控诉,他也曾说过,“在日常暴力的演进中,媒体难辞其咎”。

- 潘啵的
- 2016/7/23 9:43:13
对“媒体”的展现不仅诉诸文本,也融于“媒介”的介质。在拍摄班尼于家中枪杀女孩的场景时,哈内克巧妙地利用录像带的监视器,让我们在电影景框和录像带景框的双重景框内看到了这场戏,在媒体的互相依附中,加深对凶杀场景的视觉效果和表达强度,哈内克认为这样的安排,就像雷尼.马格利特画中的男人在镜子里看见自已一样,能够逼人思考。而在电影的最后一镜里,电影的景框囊括监控器的景框,在这个“上帝视角”里,班尼的父母被儿子揭发,被警方逮捕,而监控这个案件或故事的,哈内克以这样的拍摄手法回溯并指向正在观看的“我们”。
回到枪杀现场,更确切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看到”,而是“听到”,整个枪杀场景都没有正面展示的镜头,在录像带的景框内,班尼不断把女孩往外推,再回到镜头里拿子弹,再补枪,这个调度显然是哈内克的有意企图,当然也是足够正确的做法,拍摄人物直接死亡的画面远没有比依靠声音提供想象空间要来得更为强烈。对声音的另一套用法还见于电影结尾,哈内克设计了一场班尼在合唱团里高唱的戏码,可在我听来,合唱的乐音是缓慢又发噪的嗡鸣,在班尼全家还没获得惩罚结果之前,这股乐声催人难耐。哈内克对声音的运用好似成了一回和观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叙事交易。

- 告别摩天轮
- 2016/7/23 13:11:10
除了视觉和听觉,食物/动物在《班尼的录像带》里也是激发暴力和冲突的元素。在杜琪峰的电影里,茶餐厅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调度场景,枪战前的餐食,可在刺激观感之前先刺激味蕾神经,同样,人物的吃态也是辅佐表演抑或制造紧张氛围的绝佳手段,但在哈内克的电影里,用途并非如此。
班尼在杀害女孩之前,和她一起吃披萨喝牛奶,而杀了女孩后,他紧接着是缓缓走向冰箱开始吃优格,在之后的某个镜头里,又出现牛奶洒在地上擦拭的画面,这和班尼杀死女孩后擦拭血迹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牛奶和血拥有相同的液态,在剪辑里达成匹配,当牛奶令人联想到斑斑血迹时,很难不让人作呕。这样的方法同样在“动物”的视觉物里奏效,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杀猪场面里,我很难不把临死前发出嗷嗷惨叫的猪和临死前不断逃脱喊叫的女孩联系在一起。从视觉到听觉,从味觉到通感,哈内克竭尽所能触动我们的感官神经,调动出对暴力杀人的想象和厌恶。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